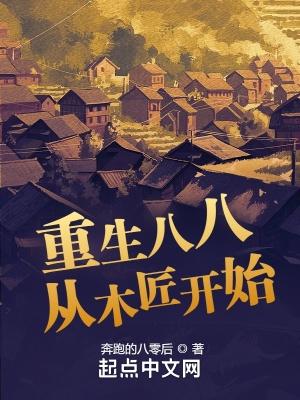零点看书>阿姆为妻 > 4550(第20页)
4550(第20页)
她翻起眉眼打量他,这个他亲手带大的男人,有着极其优越的躯体,极为英俊的面庞。
她全然体会过他的身体和灵魂,她喜欢他埋在她颈窝里,一边狠重喘息一边臀肌收缩。他的全然投入显得十分虔诚,他浑身带着欲望的动作更像是一种向她的朝拜。
她从不在这个过程中觉得他在占有她。
他在奉献自己,靠着那样的奉献,祈求她的垂怜。
她同样痴迷于此,他进攻的姿态非常迷人,她同样对他目眩神迷,她很想知道,他真正失控是什么样子?
此时她抬起手,轻轻抚弄他的面颊,他还在掉泪。
“阿姆,我只是想做更多。”
“你已经做得很多了。”
他的眼泪令她柔软下来,她躺在他结实的腿上,嗅着他身上捂了三日并不清爽的气味。
“沈樱,我这次一定会考中。”
“嗯。”她松开他的手腕,声音忽然变得冷淡,“到京城后你病情重了些,为何不说?”
陈锦时手腕撤回,眼神中添了几分慌乱。
“不算太重,吃了药都好了。”
京城气候较金陵更加寒冷干燥,喘症病根难消,就算从前控制得尚且不错,如今却又加重了。
若她不是今日掐住他脉搏探查,不知何时才会发现。
沈樱从他腿上起身,他感到失落。
“我会帮你重新调整方子,陈锦时,你先好好考完试。”
他背抵在车厢壁上,看她:“我知道了。”
马车渐渐驶近宅院,沈樱抬手理了理衣襟:“先下去吧,家里等着吃饭。”
陈锦时跟着她下车,身躯在她身后也显得高大,牢牢缀在她身后是他的习惯。
张若菱迎上来,使人替他卸下披风。
“可算回来了,你哥方才还问你。”
陈锦时解下披风,神色稍显疲乏:“我哥这么早就回来了?”
“也不早了,这几日宫里没多少事务。”张若菱在前面走着。
陈锦时却没动,脚步还黏在沈樱身后,直到她动身,才乖乖跟着往里走。
进屋,陈锦行坐在上位,见沈樱来了,起身让她,几人一坐下,丫鬟端上冒着热气的羹汤。
自年后,府上遣散了不少下人,总算不显得拥挤。
陈锦时与陈锦行在沈樱左右两边落座,看了对方一眼,谁都没张口说话。
陈锦行如今眼神愈发显得冷厉沉稳,陈锦时也褪去了那些桀骜不驯,愈发显得矜傲自持。
桌上汤羹冒着白汽,咸香漫开。陈锦行先端起碗,用汤勺轻轻搅了搅,目光扫过陈锦时眼下的青黑,语气平淡:“贡院里住得还惯?”
“还行,就是夜里有点冷,阿姆给我带了炉子,用着正好。”
沈樱指尖顿了顿,瞥了他一眼,没说话。
陈锦行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:“后日复试,我恰好休沐,可送你去贡院。”
“不用了。”陈锦时似笑非笑,“阿姆可以送我。”
陈锦行也没坚持,轻点了下头,舀了一汤勺汤羹入口。
饭后,沈樱站在廊下,张若菱递了件披风给她:“夜里风大,披着点吧。”
沈樱接过披风拢在肩上,指尖触到柔软的兔毛里子,暖意在肩头漫开。她望着院角那株刚冒芽的海棠,轻声道:“这几日辛苦你了,府里事多。”
“我有什么辛苦的呀,府里拢共才这几个人,时哥儿又是一向不要我操心的。”
沈樱刚要说话,就见陈锦时从屋里出来,陈锦行紧随其后,两人方才留在屋中说了会儿话。